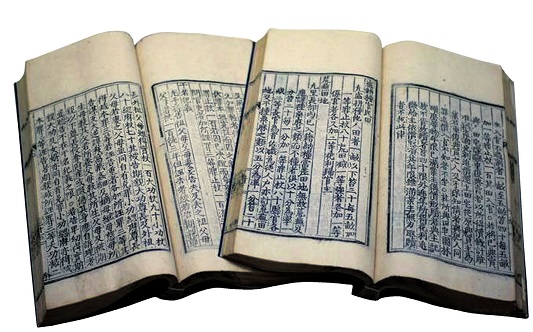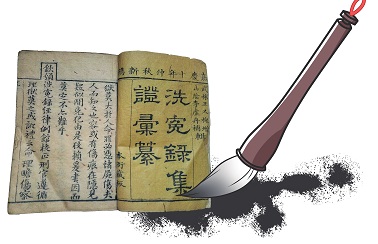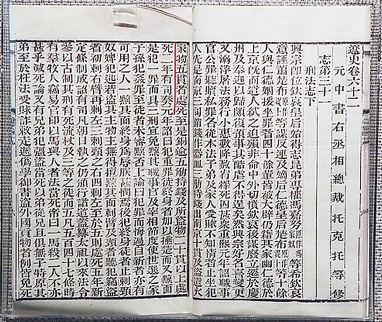明代对放火的刑事处罚
编者按
《大明律》是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典,不仅继承了明代以前中国古代法律制定的优良传统,是中国明代以前各个朝代法典文献编纂的历史总结,而且还开启了清代乃至近代中国立法活动的源流,特别是其律文结构和“轻其轻罪,重其重罪”的量刑原则对《大清律》有较大影响。有说法则直接将顺治三年(1646年)颁行的《大清律例》看作《大明律》的修订本。
另外,为把《大明律》贯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朱元璋还汇集官民“犯罪”事例来解释律条,这与今日世界通用之“以案例定罪”相当,在中国古代法典编纂史上具有革故鼎新的意义。
(栏目编辑:言西)
张晔/文
上两期中,我们对明朝关于放火和失火罪的处罚有了大致的一个概念,就是严苛和残忍。杖责之后还要流放,有的还要杀头,还有要枭首。原本这期笔者不想再看明律的,在查询《大清律例》的时候,却有点迷惑,为何所谓的清代继承明代的律例,在《大清律例》中有“放火故烧人房屋者,充军”的条例,“充军”的处罚显得特别温柔。于是笔者决定再仔细研究下明律。其实有这样的困惑是因为有律、有诰,还有皇帝的诏书。明清两代又保留了非常多的案例。
我们就先看放火,笔者参考《大明律集解附例》,其中有“放火故烧人房屋”一节。
“凡放火故烧自己房屋者,杖一百,若延烧官民房屋及积聚之物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而盗取财物者,斩,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
“若放火故烧官民,房屋及公廨仓库系官积聚之物者,皆斩,须于放火处捕获有显迹证验明白者,乃坐,其故烧人空闲房屋及田场积聚之物者,各减一等。并计所烧之物减价尽犯人财产折剉赔偿还官给主。”
我们发现,这里是将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分得非常清楚,烧民宅,杖一百,但烧公家的房屋(含官府、公房、仓库),斩首。如因烧私宅蔓延到了公家的房屋,杖一百以上,还得徒三年。这种从“徒”立刻“递进”到死刑的跨越,让人不寒而栗。因为明代依然是遵从“五刑”的原则,笞是最低的一层刑罚,到杖、徒、流、死。徒和死之间至少中间还有个流放。但若是烧公房则没有,直接斩。这种谁胆敢违逆官府就得死的意图昭然若揭。
更可怕的是,这里是不分从犯和共犯的,在注解中这样补充:“若故烧官民房屋及公廨倉库係官積聚之物,則與延烧者不同,故不分首从,皆斩”。
如果发生在宫廷中,其实刑罚更可怕。这也是为何会有放火枭首的说法。该书中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一厨役点灯,偷饮官酒,醉卧,致烧酒房,并上用等酒比放火故烧官物及盗内府财物论”。字面的意思就是一个厨房杂役点灯的时候,偷吃了宫廷里的酒,喝醉了后就倒头昏睡了(大概因为点灯,手上有火种或者灯油),导致烧了酒坊,两个情节合并处罚,比照放火故烧官物和盗内府财物论处。
如果我们完全按照明律来看,这个人是先偷盗,然后失火。根据明律中关于失火的来看,“延烧官民房屋者,笞五十。因而致伤人命者,杖一百。罪坐失火之人。若延烧宗庙及宫阙者,绞。”但是,这个厨役最后却不是以失火罪论处,而是比照了放火故烧官物及盗内府财物论处。放火烧官物,我们已经上文引用过了,斩首。“盗内府财物”在明律中是这样表述的:“凡盗内府财物者、皆斩”。其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如何判定失火还是放火,完全不是从主观意思表示出发,也许仅仅是从对象和损失的结果来判断,因为是皇宫内,总归是要死的,无论是故烧还是失火。我们仅仅从表述上就能看到这样的非故意的失火情节,但最后却冠以“放火烧官物”的罪行。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宫廷中发生火灾惊扰了皇帝,还是情节太过恶劣,之前所提到关于枭首的皇帝诏书就发布了,“成化八年六月十六曰节该钦奉宪宗皇帝圣旨各边仓场若有故烧系官钱粮草束者,拏问明白,将正犯枭首示众,烧毁之物,先尽犯人财产折剉赔偿,不敷,之数着落经收看守之人照数均赔钦此”。
我们提到过《明大诰》中极其残忍的刑罚,似乎这个枭首也仅仅是强调了死刑的一种方式,反正都是死刑范畴,只是手段不同而已。但我们注意到,在《大明律》中,对放火故烧官府财物的罪犯,提到了“须于放火处捕获有显迹证验明白者”,也就是要在犯罪现场有验证,除了口供、认证外,还需要物证。但在成化帝的诏书和引用的案例中都不复再现,反而是强调了财物损失的经济赔偿,这种不问真相的,只求严惩和赔偿的既视感,让人咋舌。